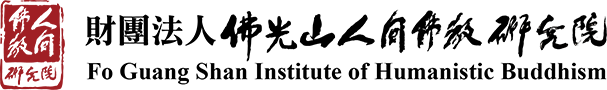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真,是人間最美的禮物!——讀《佛法真義》之感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共三冊,收錄大師各種講法而成的三百多篇短文,分為「佛法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佛門行事」等四種類型,基本涵蓋了佛教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既具有分門別類、逐一呈現的特色,又具有周全統攝、亮點紛呈的意義,同時又以舒緩幽默的文字敘說,盡顯大師直探法源、統觀全域、深入淺出的一貫風格,使讀者得以輕鬆領略佛法大海的無限風光。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的破立之道
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自序〉的結語中,提及本套書創作的背景及目的,他說:「在中國佛教裡,只有歷代的禪師們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的思考。或者有些說得不完全,只有慚愧、懺悔,唯願契合佛心,希望大家對佛法的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也請有心人與諸方大德諒解我的苦心,給予多多指教。是為序。」此段話道出了本書乃是大師面對當代佛教所遇邪教橫行問題的一種回應,而「邪教」在此應指違反佛法緣起中道者,而邪教之所以橫行乃緣於正道不昌,如果正道得以昌盛,則不只是邪教無容身之所,重要的是十方眾生才有正覺的機會。
論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詮釋之意義與價值
2019年春節前收到了佛光山寄來的星雲大師著《佛法真義》3冊,利用假期仔細閱讀,品味並讚歎大師一生為弘揚佛法而四處奔波,對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佛法真義》既是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性詮釋,也是其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真實寫照。
對星雲大師「我是佛」和黃檗禪師「即心即佛」心法的成佛可能性之理論解析
人間佛教講「我是佛」,重在承擔弘法重任,以佛的精神態度興辦各種佛化生活事業,則主觀方面讓自己意志堅定,客觀方面對社會功效宏大。從禪宗修行進路講「即心即佛」,重在一念不起,自心處在佛心境狀態,也是「我是佛」的一種表現。前者不論何時成佛,此生就做佛事業;後者亦不論何時成佛,當下就在佛心念的狀態。前者是菩提心慈悲心的當下具體操作,後者是般若實相智慧的當下具體心法,兩者相輔相成,共成人間佛教「我是佛」的最猛利法門。至於採此法門的修證者何時真正成佛,非關要務,自信最終成佛,對此之念慮,便當放下。
論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詮釋之意義與價值
2019年春節前收到了佛光山寄來的星雲大師著《佛法真義》3冊,利用假期仔細閱讀,品味並讚歎大師一生為弘揚佛法而四處奔波,對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的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佛法真義》既是星雲大師對佛法真義的現代性詮釋,也是其所推行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真實寫照。
真,是人間最美的禮物!——讀《佛法真義》之感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共三冊,收錄大師各種講法而成的三百多篇短文,分為「佛法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佛門行事」等四種類型,基本涵蓋了佛教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既具有分門別類、逐一呈現的特色,又具有周全統攝、亮點紛呈的意義,同時又以舒緩幽默的文字敘說,盡顯大師直探法源、統觀全域、深入淺出的一貫風格,使讀者得以輕鬆領略佛法大海的無限風光。
虛實之間的真相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的破立之道
大師在〈佛法真義.自序〉的結語中,提及本套書創作的背景及目的,他說:「在中國佛教裡,只有歷代的禪師們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的思考。或者有些說得不完全,只有慚愧、懺悔,唯願契合佛心,希望大家對佛法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也請有心人與諸方大德諒解我的苦心,給予多多指教。是為序。」此段話道出了本書乃是大師面對當代佛教所遇邪教橫行問題的一種回應,而「邪教」在此應指違反佛法緣起中道者,而邪教之所以橫行乃緣於正道不昌,如果正道得以昌盛,則不只是邪教無容身之所,重要的是十方眾生才有正覺的機會。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二─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日本帝國正式在台灣實施真正民眾組織化、「皇民化」政策,是在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後,依照時間序,分別是1932 年指導部落(村里),以及臺中州部落振興會的結成;1934 年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促進了部落振興運動;11935年以改善「陋習」為名、打破舊慣信仰的運動開始,隨著戰爭氣氛漸高,誕生「皇民奉公會」,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進行台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