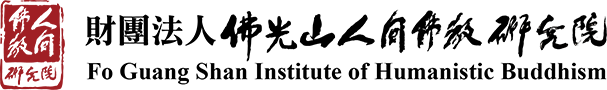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and Tiantai Thought in the Sung Dynasty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真俗相即:由《大乘起信論》論人間佛教之圓融性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為求生存與發展而不斷改革,人間佛教應運而生,並取得了舉世矚目之成就。其所以能如此者,以義理觀照之,當在於其真俗並融、人佛兼攝之理念。佛教圓融思想,萌芽於印度,光大於中國,而《大乘起信論》承上啟下,尤為淵藪,對理解人間佛教之義理含蘊及歷史意義,極具啟發。本文試圖以《起信論》「一心開二門」說為依止,復以中國哲學傳統為參證,以彰顯人間佛教之圓融精神,指出其必然性、可能性、現實性,以及張力之化解,以期消除質疑、詮釋貢獻。據本文之梳理,人間佛教圓融精神同整個中國文化生命、哲學思想有莫大淵源,其圓融性復體現於三個維度:即出世即入世,即神聖即人生,即宗教即社會。
「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
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開創者是楊仁山居士,被人們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是在比較儒、釋、道各家學說後,多次閱讀《大乘起信論》,才「始知佛法之深妙,統攝諸教而無疑也」。他自述:「鄙人初學佛法,私淑蓮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賢首、清涼,再溯其源,則宗馬鳴、龍樹。此二菩薩,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西天東土,教律禪淨,莫不宗之。遵其軌則,教授學徒,決不誤人。」所以他要「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無欠無餘,誠救補偏之要道也」。楊仁山認為佛教理論中的常住不變的是「真如」,它緣起萬法,但「本性清淨」。「真如」是佛性,是原本就有的一種心性,因此他持「真如緣起」說。遺憾的是,楊仁山居士的願望並沒有由他的弟子們完成,反而走上另一個方向。 《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佛學中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正是有了對它的爭論,掀起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首次高潮,並且一直影響了後來的佛學研究。本文即對百年來的這方面研究作一些粗淺的介紹與綜述,不足之處,歡迎方家補足。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傳譯之研究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的譯者,有二種說法:一者認為是般剌蜜帝等譯出; 另一說法則為懷迪所譯. 此經有二譯人署名的情形,顯示其傳譯極為可疑. 而作者探究此二署名的由來又皆不實,故推斷有關此經為翻譯之作的說法不足採信,可能係一偽作。 此經在中國向來被認為是真典,但在日本最初由普照請來此經時,就已有真偽之論諍. 作者認為著述此經者以首楞嚴經作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抄出之別行經,企圖以此瞞過世人; 其附以首楞嚴之題名,亦是來自《首楞嚴三昧經》. 而其教旨也有不少是根據《大乘起信論》等諸大乘經典而來,甚至和道教思想相混和. 總此原因,作者以為此經絕非梵本之翻譯,而成書年代應在久視元年 (西元700年) 後。
《大乘起信論 》的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論《大乘起信論》對禪思禪詩的影響
《起信論》對禪宗思想體系產生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在心性論上,禪宗受其心真如門的影響,表現為真心本體超越一切、自性清淨遠離垢染;在迷悟論上,禪宗受其影響,表現為對一心二門的參究、一切分別源於自心、妄執與情識是迷昧之源;在解脫論上,禪宗受其影響,表現為對無念、無我、不二法門觀念的提倡;在境界論上,禪宗受其影響,表現為始覺本覺合一、心性如鏡之圓明、真心超越分別。《起信論》通過影響禪宗思想、禪悟思維,進一步影響到表徵禪悟體驗的詩歌,從而在中國佛學史、詩學史上,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寶藏。
佛教的生命學
《大乘起信論》說,我們的心有「體大」、「相大」、「用大」,這個心,其大無比。心的「體大」,大如虛空,甚至比虛空還要大,所以佛經裡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一個人如果有容納宇宙虛空的心量,必定能做大事。心的「體大」就是生命,如果萬物沒有生命,就沒有作用了。心除了體大之外,還有相大,心的「相大」就是生死,是生命的階段性變化。而心的「用大」,就是生活。我們活在世間上,有所謂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都是心的種種作用。 生命是人間的體,生死是人間的相,生活是人間的用,體、相、用要俱全,這是佛教對人間的一個看法。本文即以「體大的生命」為題,進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