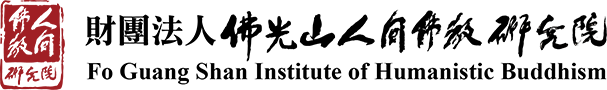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以音聲做佛事、用歌聲弘佛法——台灣佛光山梵唄與佛歌之探究
佛教認為音樂具有開示與供養等作用,因此音樂在佛教中有著很高的地位。佛教經典《中阿含經》卷29 中說道: 世尊告曰:「沙門,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汝在家時,善調彈琴,琴隨歌音,歌隨琴音耶?」尊者沙門二十億白曰:「如是,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急,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緩,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調絃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如是,沙門,極大精進,令心掉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
佛教經典藝術之流傳
星雲大師對佛教經典之管理實用的當代詮解
本文從星雲大師詮釋佛教經典之管理學內容,萃取出其中能為現代管理應用提供重要啟發的三點:品格管理、智慧管理、善緣管理。品格管理要求經理人具備良好品格美德,除了避免因其不道德行為造成企業的重大損失,更積極的意義是善巧運用某些優良品格特質,有助領導力與管理力的提升。其次,管理者除了養成優異的管理技能,還須開發無執清明的決策智慧,看清事情各面,洞悉未來情勢,作出卓越的經營決斷,而佛教的般若智慧修鍊有助開發經理人的智慧。廣結善緣的管理哲學植基於佛教的因果觀,多行善法將會帶來事業經營的助緣,與人結善緣則會減少事業成就的障礙。
從佛教的「解脫觀」看人間佛教的實踐意義――以《雜阿含經》與星雲大師之著作為依據
本文旨在探討佛教的解脫觀以及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之間,在學理上的關係。從佛教解脫道經典的《雜阿含經》整理出關於解脫的形式與內容,看出佛教所著眼的生命世界,從眾生在世間受苦的情形,提出解脫困苦的修行方法。在大致確立佛教的解脫觀之後,將探討在當代具有相當價值的人間佛教學說,依據星雲大師的著作與說法,檢視與佛教經典的解脫觀在條理、脈絡上是否一貫,以作為身處於人間修行時的一種參考。
附錄二 佛教經典與生命教育之實踐—讀解行證《維摩詰經》之「 菩薩淨土」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在現代性脈絡籠罩下的當代人間佛教,雖一方面上溯佛陀的本懷即為人間佛教的起點,但無疑的也是對現代性問題之挑戰的回應,才有當代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運動的出現。本文從兩大點來說:一是由理解經驗現象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說「人間性」;另一則是藉由經典詮釋活動,以說明「人間性」在其中的展現,並同時指出佛教經典詮釋活動所需參照的原則。指出人間性即人是在任何差別乃至對立的現象「之間」,經由自覺的反省與問題的處理而展現,用佛教的概念來說,人間性即人對其處於緣起法之間的自覺與反省。
論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之爭
宋代天台宗內部的山家、山外之爭,前後綿歷四十年,在過程上顯得極其複雜,所爭論的問題則涉及到經典及教義的諸方面。
喬達摩佛陀之凡聖問題
由於佛教流傳時間久遠,地區廣大,佛教教主不再被視為凡人,而是個超人或神。法報化三身的觀念與大乘佛法有密切關係,但小乘者,如說出世部和大眾部都認為佛陀具有異乎常人的特性。作者主張此問題應回溯到紀元前四世紀,甚至佛陀在生時,從巴利文經典的記載加以釐清。 本文分三部分:一. 巴利文獻中佛陀的超凡特性:根據《大般涅槃經》和《長阿含》,佛陀壽量無有邊際,佛陀以其威神力渡河,有天眼通,能預知未來事實,具三十二完美身相。 二. 佛陀早年的神異事蹟:佛陀的神奇事蹟似乎集中在其早年時候,如右協所生等。這些奇妙事蹟很可能是在佛教勢力鞏固,和佛陀被稱為「天人師」後,後人才加以杜撰的。 三. 佛陀如凡人的一面:論理和仁慈的行為,過王子的生活,老死之相等。又根據考古發現佛陀二大弟子遺體及佛陀出生地點,丈室,初轉法輪地的史蹟,可以合理地假定佛陀確實如普通人存在過。顯然佛陀生而為人,但入滅後被提昇為「超人」,變成偉大的神。
法華經之弘傳者「法師」的詮義探研
《法華經》乃天台宗所依之根本聖典,智者大師依此經而深獲自內證,得法華三大部的名著問世,並且成為天台宗傳承史上重要之依據論疏。故研究之首先,必以此為目標。閱讀 之初,發現《法華經》的菩薩道,竟然是以五種法師──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五種行門,作為其成佛方法,此為其他經典所沒有之特點(一般經典亦強調受持、解說的功德殊勝,但無此經如此明確點出,此五行乃成佛之要道),促使我想探討之動機。
淺議維摩詰之形象——以鳩摩羅什譯本為例
《維摩詰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又名《維摩經》、《淨名經》、《不可思議解脫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也是漢譯佛經中,文學性較強且對中國文人及其文學創作影響較大的佛經之一。該經前後七譯,今僅存三個譯本,分別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在這三個譯本中,鳩摩羅什的譯文義理信達、簡潔平易、生動曉暢、文學性極強,正如胡適所說:「他(鳩摩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