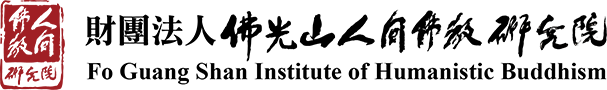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用生命感動生命——論香港蓮華分會監獄布教之成就
中國佛教過去給人的印象,基本上是出家人遠離人群,躲於山林裡出世修道,人間佛教的出現一改這種風氣。其實,佛陀之所以發願出家、說法講經,都是為了解決諸多人間問題;可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政權更替、社會變遷、思想風氣等不同的因素,佛教慢慢走入了山林之中,形成了重出世、求自了、講清修的型態。近代的大師們提出「人間佛教」並非要標新立異,而是重新審視佛陀的本懷,讓佛法落實在生活之中,令佛教重新走入人間。依循佛陀本懷,當代人間佛教的慈善事業種類之多、層面之廣,實在不勝枚舉。以佛光山的慈善事業為例,應急救難的服務就有佛光山急難救助會、冬季救濟會、友愛服務隊等;照顧人的生老病死的服務就有宜蘭蘭陽仁愛之家、雲水醫院、萬壽園等。
從《貧僧有話要說》看人間佛教之金錢觀
《貧僧有話要說》一書系統呈現星雲大師對金錢的看法,這是對佛教金錢觀的繼承與最新發展;星雲大師直承佛陀本懷,繼承「佛說的」,也提倡人間佛教之「人間性」一面,即「人要的」。星雲大師鼓勵在家眾賺取淨財,從事正當的佛教事業,但要德財兼備;對於出家眾,對於佛光山,可以從事非營利佛教事業,但儲道不儲財。星雲大師金錢觀更加圓融,且對佛教事業與市場經濟關係都有所指導。未來佛教界要合理開發金錢來源,要謹防金錢對人心的吞噬,注重佛教戒律對金錢的管制,在財產分配和財務上要更加公平公開。星雲大師在金錢觀上仰承佛陀,並以「人本位」為主體的思想,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豐富內容的具體體現。
神祕帷幕的剝離與人間佛國的踐行——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感
眾所周知,星雲大師對佛教之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15 年程恭讓先生就撰寫了一篇〈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從「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創建高素質與規模化的人間佛教僧團」、「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佛教國際版圖的大幅拓展」等十個面向進行了全面闡述。而本文只想就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作,談談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從圓仁入唐求法巡禮經歷看大運河與海路之連接
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經歷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歷可分為遊歷與求法兩方面。借由圓仁遊歷視角,海上絲路與大運河至少在唐代時已實現了客觀上的有效溝通。經由圓仁求法視域,海上絲路可通過部分居留處實現經由大運河與其他陸上絲路連接,為實現中外佛教文化的思想連繫搭建了橋梁。這些特殊交通樞紐位置中的佛教交流,也為圓仁的佛教融合與改造思想提供了精神內核。無論是遊歷抑或是求法,最本質的特徵是其中所蘊含的人間佛教的交流性,通過河海間「融合尊重」的交流,可匯成人間佛教學的信仰合力,實現信仰之躍。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從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使用,弟子對「四句教」的賡續,學者對「四句教」的重視,均可見「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的?「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之學術詮釋與省思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一部結合理論建構與實踐歷程的宗教思想巨作,全面記錄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理念、組織建設與全球拓展的歷程。本文從學術研究角度出發,透過宗教思想史、社會學與跨文化交流等觀點,系統梳理本書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文化教育慈善實踐、僧信制度建設、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策 略,以及對台灣佛教轉型的深遠影響。進而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不僅是星雲大師個人修行與弘法的總結,也是人間佛教作為當代宗教現代化、全球化範式的重要文本,展現了宗教回應現代社會與未來挑戰的積極可能性。
《寶性論》新譯新解(之二)
《作為思想的近代佛教》第六講: 大乘佛教的實踐——從研究的視角出發
《系列大乘佛教》全10冊(春秋社,2011-2014)是《講座.大乘佛教》全10 冊(春秋社,1981-1985)的續集。我有幸入選該系列叢書的編輯委員。該系列第1 冊的主題是 「什麼是大乘佛教」,但如何對「大乘佛教」進行定義這件事本身就是極為困難的。
人間佛教與東亞大乘佛教的現代化轉型
以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為代表的的人間佛教理念和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使得大乘佛教這一古老的思想體系和實踐體系不僅在現代性衝擊面前屹立不倒,而且如老樹發新芽,為當代社會貢獻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和正面的社會效應。
《往事百語》的生命敘事與終極療癒
近幾年來,文學治療學進入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敘事治療為當中運用最廣的理論方法。「人的生命意義何在?」「人的終極價值為何?」「存在是否有其必要?」諸如此類的問題,恆困擾著歷史上每一個獨特善感的靈魂。在每個時代的現實生活中,若得不到鎮定且安心的答案,文人思想家的生命將變得苦悶、憂鬱。於是,生命的創傷與療癒,乃成為人文學科新興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