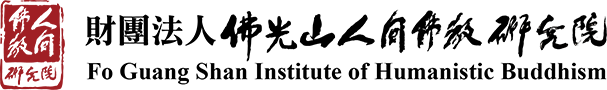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從《勝鬘經》看佛教的社會思想理論
佛教思想信仰中社會思想理論的部分,是佛教思想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大乘佛教中非常重要的理論領域。因為大乘佛教以其對於最高圓滿覺悟的不懈追求,對於眾生、社會的強烈承擔精神及救度意識,表現出比傳統佛教更為突出的社會向度的參與色彩。而在近現代人間佛教所推動的佛教轉型發展中,如何合理實現佛教「社會化」方向的轉型發展,更是佛教的重大理論、實踐課題。為此,鑑於對於佛教社會思想理論的研究一直是傳統佛學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本文以印度三世紀中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勝鬘經》為中心,對此經包含豐富深刻的佛教社會思想理論予以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和評述。
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及佛光淨土的創建
在佛法的管理思想中強調使用者的行為,而其行為導自於心性修練。星雲大師的管理信念告訴我們,在佛法中「管理」能給予我們什麼?我們應在哪些情境下如何使用佛家的管理方法?尤其是心性修練這個關鍵內涵。這是本文處理的第一個問題,其中分別以「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管理者須先自我管理並具用人授權之氣度」、「管理者須能悲智雙運並具同體共生之理念」等三個面向來闡述。 本文第二個問題是接續第一個問題而引發,討論建立佛光淨土與管理思想的關係,其間以大師對彌陀淨土的讚揚、取法為開端,進而論述藉由阿彌陀佛的管理思想,亦步亦趨地建設佛光淨土。處理上述兩個問題,主要在於檢討星雲大師實行人間佛教,既而建設人間淨土、佛光淨土的種種施設。基此,本文之主軸在於「人間淨土」如何建設,以及「佛教徒的修持」應有的體認及態度,「管理」只是假說,亦是俗諦,佛教徒可藉用「管理」的指而逐步完成淨土的建設。
漢文佛教大藏經的刻印—兼談《佛光大藏經》的編纂
一千多年來,中國佛教界和朝廷刊刻了二十多種大藏經。最初的編纂者是以《開元釋教錄》的紀錄為基礎,他們的責任是按先前的某版本,儘量收集齊全。然大藏經多被藏在藏經樓裡,使得承載佛陀教導的大藏經,其淨化人心的功能無法發揮出來。《佛光大藏經》是中國大藏經發展史上,第一部旨在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大藏經。它是以民間的力量編纂的。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現代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隨著紙本和數據化的大藏經的普及,佛法能通過大藏經延續和流傳。《佛光大藏經》的貢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信願行解的隨身寶:《佛光大辭典》
藏經是佛教學的的寶庫,歷代對藏經的編纂極為重視,不僅當作政績大業,也視為傲人文化成就。編纂戴經,勞師動眾,費力耗時,亦末必能成,一個朝代又往往只能完成一次編修工作,這也可能是有的機會。藏經編纂之巨困難如此,而一位佛教學者想攀足藏經高閣,即使窮其畢生之力勉勵精進,又能閉關幾度?閱藏幾許?其親證佛語奥義又幾番?要能悠遊經藏法海而不迷失,除了憑其毅力和因緣外,就只能依靠工具了。辭典就是出牌迷津的普巧工具,是佛法經法海的舟輯。
印度佛傳圖的象徵藝術
佛一生的事蹟,被印度的藝術家及佛教的僧侶們,雕刻描繪在寺院石窟之中,具有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可追自西元一、二世紀的印度貴霜王朝(Shunga) 到九世紀末的帕拉王朝 (pala)。佛傳的主題深深地吸引著藝術家們,如像當時佛教的信眾,對於佛教犧牲奉獻的熱誠,佛教藝術的盛況就像這豐富的遺產般瑰麗奇偉。藝術家和僧侣們從早期佛教文學中文學尋找題材,雕刻描繪在佛塔浮雕或石窟壁畫上,使整個佛教藝術呈現磅磚的氣勢。
佛光山叢林學院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曾說過:「沒有教育,縱有再高深的教理,再眾多的經典,誰去研究呢?所以必須要提倡教育。僧伽,要有僧伽的教育;信徒,要有信徒的教育;甚至於兒童、婦女,也要有兒童的教育,婦女的教育。」這樣的因緣開展佛光山一心辦教育的理念。
值得信賴的法寶——讀《佛光教科書》有感
拿到佛光山印行,星雲大師編著的《佛光教科書》,雖然淺學輒止,卻也受益良多。聯想起自己初學佛時,因既沒有良師指導,又沒有找到應機的佛學入門書籍,而走了不少彎路,所以,當我瀏覽此套叢書之時,相見恨晚之感油然而生。因此,藉此文章,一方面向有心學佛又不知從何入手者推薦此書,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初學佛時所遇困境提供給讀者以為經驗,希望後來者能因此少走些彎路。
劉禹錫與佛教
中華佛教,特別是學術,自隋代開始「獨立」後,入唐即稱鼎盛,廣泛影響國人生活,唐代如韓愈等排佛崇儒的儒學名家,尤係如此. 劉禹錫生來,其性即聰慧不凡,自幼受到佛學熏染,深得名僧靈澈,皎然器重,故其學問大成以後,茍為文,則多見反應其直接間接受了釋門學術的深刻影響; 若為詩,則多見表現其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的特別欽仰. 本文作者輯錄集本,外本所收,經劉氏吟和的詩歌,其中充分表現他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特別欽仰者,並用全唐詩內所收新編十二卷劉禹錫詩,相與校對付印. 由這些作品可明顯看出,劉禹錫自幼即與中國佛教佛學及佛化,結了不解之緣,亦可獲知他個人不厭其煩地反復表白,個人由愛佛而信佛,深受佛教佛學的影響。
再現佛法真義,回歸佛陀本懷——讀星雲大師新著《佛法真義》
人間佛教就是真正的佛教。它不僅僅是一個佛教界提出的口號,也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主張,它是佛教形成以來就擁有的弘法利生的實踐方式,也是一種新型的思想體系與信仰結構。 真正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因為人間佛教把出家和在家、出世和入世、寺院和家庭、山林與都市、男眾與女眾等等一切都融合、完整、圓滿了。為此,能夠體現這種圓滿、完整與融合的實踐體系的思想與信仰,就是最能有利於當代人間社會的佛法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