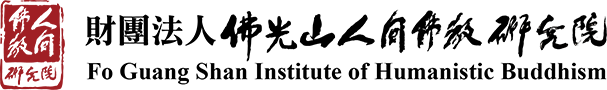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論《人生觀的科學》中太虛大師與梁漱溟的文化理論互動
從「善巧」到「靈巧」—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靈巧人」形象
中道的視域融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詮釋學淺論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 中國佛教當代發展的方向
中國佛教尤其是大陸佛教的發展在今天面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誠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但毫無疑問,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是從太虛大師提出的一直到星雲大師所發揚光大實踐推動的人間佛教。在這裡,我想就個人對大陸當代佛教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人間佛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成功實踐談談自己的看法。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人間佛教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芻議
過去三十年,經濟方面的台灣經驗已經深刻的影響中國大陸,接下來三十年,文化教育方面的台灣經驗如何影響中國大陸,將是兩岸關係的重點。北京的光中文教館、上海的星雲文教館,均將在今年完成投入使用,建議可以開展人間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的三十年計畫。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
本文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由太虛大師所倡導,近現代以來在台灣、東南亞一帶興起的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現代化問題,認為人間佛教旨在提供一種生活的藝術,其精神實質即「以出世的精神作人間的事業」。它不僅是中國佛教在傳統文化背景上歷史的邏輯發展,而且也是在現實環境下,為迎接時代生活的挑戰,而邁向現代化的一種巨大努力,從文化現象上講,它又是一種由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文化轉移和滲透,人們常稱之為「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