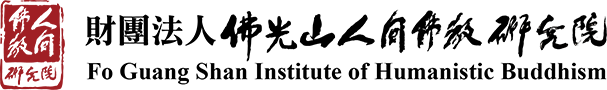站內檢索
站內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僧信觀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僧信觀,以僧信平等為基本理念。繼承原始佛教以布施為結構性基礎的僧信關係,以及佛陀制戒為原則的倫理保證,是對傳統中國佛教中「僧尊信卑」、「尊信抑僧」、「僧信平等」的再詮釋,尤其是「在家能作師」問題上,最具突破性的理論與實踐貢獻。早期部分信眾的貢獻,為制度化建設僧信體系具有重要經驗意義;國際佛光會的創建,尤其是檀講師制度的設立,是提高信眾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措施;71 位台灣本地檀講師的教學實踐,為台灣佛教尤其對人間佛教的推動具有實踐意義。總之,星雲大師僧信觀理論與實踐,既是「佛法生活化」,又是「生活佛法化」的表達,也力圖構建僧、信二眾均衡、團結的現代佛教團體,使僧、信二眾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的展望
本世紀二○年代後期,太虛大師(西元一八八九-一九四七)針對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的積弊,提倡以重視人生和改善人生為基礎的人生佛教,為此而奮鬥了一生。此後,太虛大師的弟子和受到他影響的人們,又進而提出強調社會現實性的人間佛教的思想。進入八○年代,海峽兩岸的佛教界和其他華人居住的地區,都積極提倡並且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有更多的學者對此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人問佛教的提出和付諸實踐,代表著中國佛教已進入新的重建過程,正在適應現代社會巨大的變革。展望未來,人間佛教將怎樣發展,呈現怎樣的面貌,對社會將產生什麼影響,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僅據所掌握的部分情況,從史學角度作些預測,並以此向專家讀者請教。
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自利利他 僧伽的雙重責任
中國佛教經歷隋唐時期的輝煌,漸趨頹勢,降至清末,烽火不斷,民不聊生,不少出家人不得不以「超度亡靈」的法事活動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呷教的和尚」,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超亡送死」的「死鬼佛教」。太虛大師對此怪異現象有如下評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典範重塑——從《畫說十大弟子》談佛教生命教育的當代實踐
本文試從佛光文化出版的《畫說十大弟子》改編僧傳著手,探究如何透過改編重塑聖者的當代形象,並以此建構當代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 透過視覺的圖象符號分析,認為此書運用不同媒介系統的結合形塑聖者形象為其改編特色,而運用照片、圖畫等不同媒介系統所再現聖者形象的內涵,一是以佛教照片的事實引用,協助讀者在其自身的文化脈絡下感知符號的意義;二是運用圖畫語彙翻譯並重顯抽象的佛教觀念。而對於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則分從二部分探討。一是在文字與圖象的交互指涉中,探究生命意義空缺如何由讀者填補,並在填補中開展自身生命的意義。另外,則從讀者接受及詮釋的理解中,探究適應讀者接受而建構的生命教育範示,其內涵有三:一是慧命承襲的共同典範。二是教育的學習模範。三是建構學佛者的聖者典型。
元代佛經譯僧沙囉巴
唐代僧籍管理制度
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